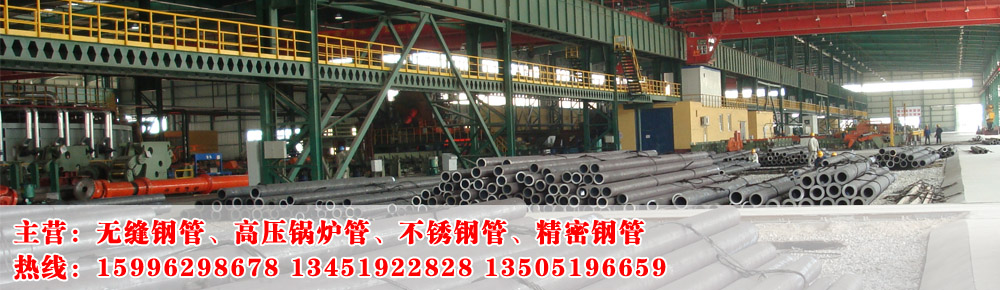保障性住房建設(shè)涉及面廣、公益性強(qiáng)、社會影響大。隨著近兩年急劇提速,保障房建設(shè)暴露出諸多問題,不少地方在保障房申請、審批、質(zhì)量、分配等環(huán)節(jié)面臨監(jiān)管考驗(yàn)。
專家表示,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不僅涉及土地、規(guī)劃、建設(shè)、資格認(rèn)證、分配、退出等多個(gè)管理環(huán)節(jié),還需統(tǒng)籌協(xié)調(diào)規(guī)劃、財(cái)政、建設(shè)、房管、民政等多個(gè)部門,因此,地方相關(guān)部門應(yīng)相互配合,各司其職,形成監(jiān)管合力,堵住漏洞,把保障房打造成民心工程。
本質(zhì)回歸:莫讓“保障”成“福利”
從最早的經(jīng)濟(jì)適用房到后來的限價(jià)房再到如今的廉租房、公租房,有一個(gè)問題一直是監(jiān)管的重中之重,那就是保證保障房的保障本質(zhì),莫讓其成為部分人的福利房。
中國房地產(chǎn)學(xué)會副會長陳國強(qiáng)向《經(jīng)濟(jì)參考報(bào)》記者表示,此前,借保障房之名實(shí)現(xiàn)福利分房目的的現(xiàn)象確實(shí)存在;另外,各地保障房進(jìn)入及退出機(jī)制仍不完善,進(jìn)入門檻不嚴(yán),標(biāo)準(zhǔn)執(zhí)行流于形式,而不健全的退出機(jī)制使得保障房成為部分人的牟利工具。這些現(xiàn)象都嚴(yán)重侵害了保障房的保障本質(zhì)。
也有專家指出,關(guān)于此前“保障房或成福利房”的爭論,要多因素來看。一是保障房制度演變的歷史因素,1998年時(shí)設(shè)定的供應(yīng)對象范圍較寬泛,一些中等收入群體也購買了經(jīng)適房,這導(dǎo)致一些對房改不熟悉的人簡單地認(rèn)為“經(jīng)適房賣給了有錢人”。二是由于部分保障房的“共建性質(zhì)”。根據(jù)政策規(guī)定,一些合理“共建”的“單位租賃房”也被統(tǒng)計(jì)入廣義的“公租房”中,讓不明就里的群眾認(rèn)為保障房成為“單位房”。三是個(gè)別地區(qū)確實(shí)存在保障房分配不公問題。
近年來,各地主管部門開始著力監(jiān)管,在多個(gè)管理環(huán)節(jié)齊發(fā)力。今年3月,住建部更是要求各地完善監(jiān)管機(jī)制,完善申請、審批、公示、輪候、復(fù)核制度,建立信息共享、部門聯(lián)動的審查機(jī)制。天津、安徽等地亦相繼出臺保障房管理新政,針對保障資格審核標(biāo)準(zhǔn)、操作辦法、監(jiān)督方式和退出機(jī)制提出了更嚴(yán)密的方案。
全國工商聯(lián)房地產(chǎn)商會會長聶梅生向《經(jīng)濟(jì)參考報(bào)》記者表示,保障房監(jiān)管發(fā)力非常及時(shí),也很有必要。本輪調(diào)控著力點(diǎn)就在于一“壓”一“抬”,即壓商品房價(jià)格、抬保障房建設(shè),這兩點(diǎn)不能出現(xiàn)短腿現(xiàn)象。
在老百姓眼中,保障房是名副其實(shí)的“解困房”。上海退休職工夏勤誠和老伴在市區(qū)新樂路100弄一間僅8平方米的老公房中“蝸居”了20多年。去年,老兩口申請了上海的共有產(chǎn)權(quán)房,最終通過層層審核,以每平方米5000元不到的價(jià)格購買了松江區(qū)新凱家園一套47平方米的新房。談到此事,老兩口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。據(jù)了解,僅去年一年,上海就有3.7萬戶家庭受益于共有產(chǎn)權(quán)房。
欠發(fā)達(dá)地區(qū)也“不拖后腿”。在甘肅定西市區(qū)的保障房小區(qū)瑞麗家苑,病退職工姚建紅剛搬進(jìn)新家。她曾在市郵政局倉庫改建的宿舍里住了10多年。去年,政府推出可以購買一定產(chǎn)權(quán)的廉租房,姚建紅借錢湊齊5萬元,買下了這套49平方米的一居室。“原來宿舍沒有自來水和暖氣,現(xiàn)在這條件,我們已經(jīng)很知足了。”
潤滑設(shè)備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