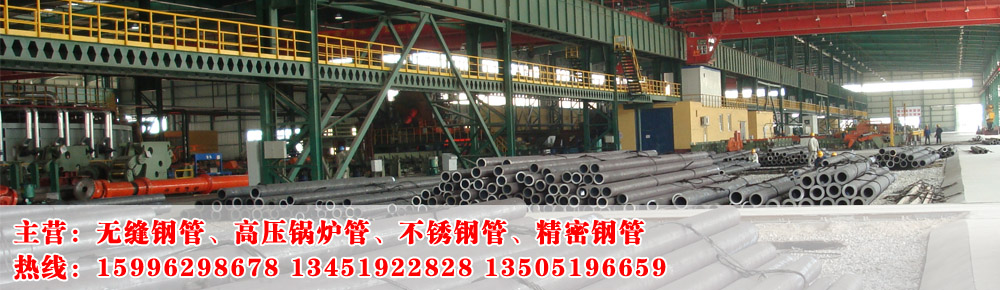1985年,臺(tái)灣大學(xué)中文系教授臺(tái)靜農(nóng)依然住在臺(tái)北市溫州街龍坡里的舊式庭院中。這是臺(tái)大時(shí)光最久的一棟宿舍,木質(zhì)的老樓已經(jīng)有百年歷史,走在屋里地板咯吱咯吱響。從1946年應(yīng)許壽裳之邀渡海來臺(tái),浮沉40載,往事大多已經(jīng)沉入記憶的湖底。
之前他的學(xué)生蔣勛赴歐洲讀書,才從陌生的《魯迅全集》中驚奇地發(fā)現(xiàn)了另一個(gè)“臺(tái)靜農(nóng)”——大陸上世紀(jì)20年代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的代表作家,“五四”時(shí)文學(xué)社團(tuán)“未名社”六君子之一,亦師亦友的魯迅評(píng)說,這個(gè)喝著新文化乳汁長(zhǎng)大的安徽農(nóng)家孩子,能銳氣十足地將“鄉(xiāng)間的死生,泥土的氣息,移在紙上”——他的老師,名中嵌有也確實(shí)不負(fù)一個(gè)“農(nóng)”字。
當(dāng)年那個(gè)狂熱追求文學(xué)理想,數(shù)度因辦刊物而入獄的臺(tái)靜農(nóng)已經(jīng)不在了。在島上象牙塔里躲避風(fēng)雨的臺(tái)靜農(nóng),頗有些魏晉名士?jī)?yōu)游卒歲的派頭,煙酒不離左右,口不臧否人物,不教唐詩宋詞而專講屈騷。有人勸他寫回憶錄,但往事對(duì)他來說好像“一張封塵的敗琴”,偶被人撥動(dòng)發(fā)出聲音來,“可是這聲音喑啞是不足聽的”。
這也不奇怪,帶著左翼文學(xué)影子去臺(tái)的臺(tái)靜農(nóng),在島內(nèi)高壓文化氛圍中選擇“靜”字當(dāng)頭,“時(shí)弄毫墨以自排遣,但不愿人知”。有一陣子他家門口經(jīng)常停著一輛軍用吉普,很多人認(rèn)為是監(jiān)視他的,他卻“澄清”說,那是因?yàn)閷?duì)門住的是彭明敏而已。
那時(shí)溫州街的庭院依舊寂寂。古舊的木格窗前有兩張紅木書桌,六把藤椅,桌角上一盆小葉蒼蘭終年舒展,每到夏天臺(tái)風(fēng)季節(jié)就開出很多花兒來。院子里有兩叢莎勒竹,臺(tái)北時(shí)常陰雨綿綿,雨落竹梢,早也瀟瀟,晚也瀟瀟。
庭院里的書房名為“歇腳齋”,揭示主人原無久居之意,結(jié)果造化弄人,一歇便是后半輩子。有人曾問臺(tái)靜農(nóng),為何不趁1949年左右的空隙重返大陸。他給出的說法頗有《世說新語》里面常有的機(jī)鋒:“實(shí)在是因?yàn)榧揖焯啵狈教鞖饫洌馐且蝗艘患^冬的棉衣就開銷不起。臺(tái)灣天氣暖和,這一項(xiàng)花費(fèi)就省了。”
省了花費(fèi),卻也跟當(dāng)年筆下的鄉(xiāng)土永遠(yuǎn)別過,此后的日子只能“老去空余渡海心”了。晚年臺(tái)靜農(nóng)喜歡吟詠金人元好問的句子:“忽驚此日仍為客,卻想當(dāng)年似隔生。”或許冥冥中自有注定,他身為臺(tái)姓子弟,勞作于講臺(tái),終老于臺(tái)灣。
1985年3月末的一個(gè)下午,學(xué)生李渝前來溫州街小院拜訪,適逢主人不在,李渝兀自在里面翻書讀史。夕陽西下,李渝悄悄給老師研好墨,帶上門出來走到大街上。多年后恩師已經(jīng)不在,小院也早舊痕無存,李渝回憶起那次未曾謀面的拜訪:“溫州街的屋頂,無論是舊日的青瓦木屋還是現(xiàn)在的水泥樓叢,無論是白日黃昏或夜晚,醒著或夢(mèng)中,也會(huì)永遠(yuǎn)向我照耀著金色的溫暖的光芒。”
據(jù)說臺(tái)靜農(nóng)晚年曾出過一個(gè)上聯(lián):“臺(tái)灣臺(tái)北臺(tái)大臺(tái)靜農(nóng)”,長(zhǎng)時(shí)間無人應(yīng)對(duì)。而自1990年他去世以后,更沒人記得去對(duì)下聯(lián)了。
君愿一試?(記者 任成琦)
潤滑設(shè)備 |